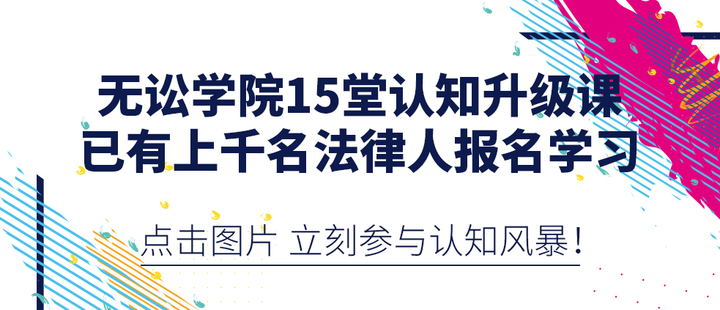本文为作者向无讼阅读独家供稿,转载请联系无讼阅读小秘书(wusongyueduxms)
合同解除是合同法上的重点内容,也是实务上的热点问题,本文选取与合同解除密切相关的数个重点问题,通过理论分析和实务案件研究,以期达到厘清这个制度体系结构之目标。思有未尽之处,求教于方家。
一、合同解除在合同法上的定位:从相关联概念之区别展开
根据《合同法》第91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消;(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在我国合同法上,第六章命名为“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合同解除和清偿、抵消、提存、免除、混同等一样,作为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一种事由。但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清偿、抵消、提存、免除、混同被规定为债之关系的消灭事由;其二,终止和消灭并非一个意思,“终止”一词有其独特的含义;其三,解除被认为是债之效力,而与清偿等五种债之消灭情形规定在不同之处。
以下就“终止”、“解除”和“消灭”等概念进行分别阐述,以明晰其不同。
(一)“终止”的含义
终止,或者称为契约终止,指的是当事人基于终止权,使继续性的契约关系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
终止权是一种形成权,可以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当事人行使终止权后,仅使契约关系向将来消灭,不产生恢复原状等效力,即终止前的契约关系仍然是存在并有效的。
(二)“解除”的含义
解除,或者称为契约解除,指的是当事人一方基于解除权,使契约效力溯及消灭的一种行为。
解除权同样是一种形成权,可以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后,未履行的部分不再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要进行清算,将产生恢复原状等效力。
从定义上可以看出,终止和解除的性质是类似的(效力上有所差异),并且在传统债法谱系上,契约终止和契约解除都被认为是契约效力或者债之效力的一部分。
(三)债之关系消灭的含义
债之关系的消灭,指的是债之关系,因为某种原因,客观上导致其不存在。
笔者认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如下几点要说明:
1、债之关系的消灭宣告了当事人之间债之关系的结束。从规范角度来说,当事人之间债之关系已经终局性地失去了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再有债权债务关系。
2、终止和解除之所以被规定为契约之效力,是因为一方当事人可以行使法定或约定的终止权(解除权),行使形成权是契约效力的一部分。
终止和解除固然有债之关系消灭的含义在其中,但它们还有其他法律效力。在终止情形下,契约只是向将来失去了效力,终止权行使之前的契约关系仍然是有效的,尚未履行的仍需要履行;在解除情形下,契约确实因解除而失去了效力,但当事人之间要对解除前的契约关系进行清算。
3、合同解除和合同终止的区别,上文其实已经都分析过,主要区别在于合同终止无溯及力,而合同解除有溯及力。承认合同解除有溯及力有利于把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相区别(《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238页)。
笔者之前认为,既然我国合同法将解除划归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章节中,不妨就将合同解除作为合同消灭的一种的情形,但要将解除与清偿、抵消、提存、免除、混同等进行区分,特别关注合同解除将产生的法律后果。
后经思考认为,上述见解其实还是没有深层次说清楚合同解除(主要指法定解除)在合同法上的体系定位。合同解除后,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准确说是消灭或结束),这只是合同解除的结果,而非合同解除的本质。站在形成权行使的角度而将其认为是契约效力的看法,亦非合同解除的本质,这只是合同解除权的性质。
笔者现认为,应将合同解除的性质理解为违约责任的责任形式(下文将分析)。当然,有人会提出,我国合同法还规定了不可抗力解除,这并不属于违约责任范畴。其实已经有学者认为,不可抗力解除不应放在法定解除中,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便自动解除,不需要任何一方行使解除权(大陆法系国家民法通常就是如此规定的。更有学者认为,不可抗力而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此时自动解除应可理解为当事人的意思,因为当事人之间不会约定发生不可抗力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时,仍需要履行合同,参见解亘:《我国合同拘束力理论的重构》,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二、合同解除的类型
合同解除分为合意解除与单方行使解除权,其中后者又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合意解除规定在《合同法》第93条第1款,约定解除规定在《合同法》第93条第2款,法定解除规定在《合同法》第94条。
《合同法》第9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第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再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关于合同解除的三种类型,我《合同法》通过前后紧挨的两个条文予以规定,似乎三者联系很紧密,但笔者在此要着重强调三者之间的区别,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合同解除类型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
对合意解除来说,其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解除某个合同,并无任何一方行使解除权,因而学说上有认为合意解除与解除制度相去甚远,似不应放在解除制度中。
对约定解除来说,其虽是一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合同,但其解除权来自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因而其法律研究的意义不是特别大。
真正对解除制度有重要意义的是法定解除,究竟哪些法定情形下,当事人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对当事人利益影响巨大,因而对法定解除情形,须特别研究。
三、法定解除的事由
法定解除分为一般法定解除和特殊法定解除,前者规定在《合同法》第94条,后者则分散规定其他民事法律中。本文主要以一般法定解除展开。
《合同法》第94条实际上区分了两种法定解除事由,一是不可抗力解除事由,二是根本违约解除事由。
(一)不可抗力解除事由
民法上关于不可抗力,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不可抗力的定义,二是不可抗力发生后的法律效果。
关于不可抗力的定义,规定在《合同法》第117条第2款: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这一定义为《民法总则》所沿用,规定在《民法总则》第180条第2款。常见的不可抗力情形有严重自然灾害、战争、社会异常事件等。
关于不可抗力的效力,明文规定在两处,一是《合同法》第94条,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是《合同法》第117条第1款,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从上述法律条文可以将不可抗力的法律效力解释归纳如下:
1、一方因不可抗力导致违约的,可以免除违约责任;
2、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3、不可抗力事由结束后尚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应继续履行合同。
(二)根本违约解除事由
根本违约解除事由规定在《合同法》第94条第2、3、4款,从法律条文内容来看,并非发生违约行为就可以解除合同,应首先考虑违约行为的严重程度,只有当合同的“主要债务”得不到履行或者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守约方才可以解除合同。
关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本违约)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可综合考察以下因素:
1、违约部分的价值或金额与整个合同金额之间的比例关系;
2、违约部分对合同目标实现的影响程度;
3、在迟延履行中,时间因素对合同目的实现的影响程度;
4、违约的后果及损害能否得到修补;
5、在分批交货合同中,某一批交货义务的违反对整个合同的影响程度;
6、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形下,当事人期待通过合同而达到的交易目的往往无法实现。(具体分析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410页)
从根本违约解除事由来看,解除制度是建立在违约行为基础之上的,因而可将合同解除理解为违约责任的责任形式。当发生根本违约解除事由时,守约方既可以选择要求违约方承担传统的违约责任(如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也可以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四、解除权的行使及解除异议的处理
《合同法》第96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解除权的性质是形成权,只要解除权人一方意思表示就可以解除合同,只不过解除的通知是一种需要相对人受领的意思表示,解除合同的通知自达到对方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就《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而言,解除权的行使一般仅须向对方当事人作出解除的意思表示,不需要请求法院作出宣告合同解除的形成判决。不过在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当事人须请求法院解除合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
理论和实务上的一个难点问题是解除异议的性质。《合同法》仅仅规定了合同相对方有异议的权利,即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异议的期限及异议的效力。《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该司法解释条文的内容有如下三层:一是如果非解约方在异议期间内没有起诉行使异议权,无论解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合同都在解除通知到达时解除;二是异议权须以诉讼方式行使;三是异议期间的性质是除斥期间。(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
从立法本意来说,规定合同解除异议期限,是为了尽早稳定合同关系,防止一方滥用权利。立法本意是好的,但该司法解释却存在致命的缺陷:从形式角度理解,如果解约方并没有法定解除事由而解除合同,相对方因各种原因,三个月内没有行使异议权,解约方居然可以随意解除合同,这是不合理的。而换做从实质角度理解,解约方解除合同需要有法定解除事由,则法院势必要对解约方行使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这就意味着司法解释规定的三个月的异议期限将是毫无意义的具文。
这两种观点在司法实务中均有体现。在“重庆泰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重庆佳路机电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即是从形式角度来理解该司法解释,该案收录进《人民司法》(2013年第24期)后提取的裁判要旨如下:符合合同解除形式要件的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未在约定或法定期限行使异议权的,异议权丧失,合同无争议的解除。如果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无权解除合同,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异议方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解除责任并赔偿损失。而在“四川省聚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达州广播电视大学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10期)中,最高人民法院似倾向于从实质角度理解解除异议制度,即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不符合约定,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权行使条件,其通知解除的行为,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理论分析和实务案例表明,上述司法解释存在逻辑困境,如何理解适用该条规定,值得反思。对此困境,有学者提出如下建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的合同解除异议权,在性质上理解为提起确认之诉的诉权,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享有,彼此诉权相互制约,以尽早稳定合同关系。法院在适用该条时,应当对是否有解除权进行实质审查(贺剑:《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研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
最高人民法院及学者实质审查的观点,值得赞同。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合同一旦解除,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巨大,因而对合同解除权应严格限制,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因而行使合同解除权,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合同解除提出的逾期异议也只是导致非解约一方当事人的异议权(形成抗辩权)消灭,解约一方当事人的解除权并不因此自动成立,解约行为也不因此自动有效,也必须满足《合同法》所规定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民事卷二(新编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6页)。至于解除合同的确认之诉中合同效力解除的起算时点,如采实质审查观点,应认为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的,如对方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效力的,在法院判决下达之前,合同不产生解除的效力(宋晓明、朱海年、王闯、张雪楳:《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的疑难问题》,收录于《合同案件审判指导》,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五、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
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主要规定在《合同法》第97条,该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这一条中,恢复原状、其他补救措施与赔偿损失分别是什么意思,理论上争议颇大。实务适用中似乎没有争议,但相关判决结果显示,法院适用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处于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
就理论学说上看,主要是围绕恢复原状性质来展开理论构建的,目前主要有直接效果说和折中说。
(一)直接效果说
直接效果说以崔建远教授为代表,其认为合同因解除而溯及地归于消灭,尚未履行的债务免于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发生返还请求权。
关于恢复原状的性质,崔建远以我国未采纳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为由,主张恢复原状应为所有物返还。也有观点认为,恢复原状性质上是不当得利返还,比如在“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泳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提取的裁判摘要认为: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是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解除合同的后果、违约方的责任承担方式不表现为支付违约金,而是返还不当得利、赔偿损失等形式的民事责任。不当得利返还的观点似乎是最高人民法院一直的观点,在更早的“重庆中建工程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等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同样认为合同解除后,一方依据协议而取得的相关利益失去了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值得说明的是,如采不当得利返还的观点,应以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为基础,但最高法院并没有这样的论证过程而径直得出了不当得利返还的结论。
对于“赔偿损失”的性质,崔建远教授认为是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这与直接效果说明显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之处。反对直接效果说的学者认为,合同既因解除和溯及地归于消灭,何来履行利益之说。更深层次的推演应该是,在直接效果说下,不应该存在赔偿损失。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早期学说即采纳直接效果说,其相应的债法部分便规定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只能择一行使。在上述“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泳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一审法院似乎认识到这一矛盾,将“赔偿损失”解释为一种基于解除产生的独立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与《合同法》第107条的违约责任区别开来,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没有说明合同解除的“赔偿损失”和违约责任的“赔偿损失”,究竟有什么区别。
(二)折中说
折中说以韩世远教授为代表,其认为合同解除后,对于尚未履行的债务自解除时归于消灭,对于已经履行的债务并不消灭,而是发生新的返还债务。
在折中说下,由于解除并非使合同溯及既往地归于消灭,因而,恢复原状义务被认为与本来的债务具有同一性。解除前的受领仍然具有相应的法律上的原则,故原状恢复义务并非不当得利返还。但是,恢复原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理论见解并不统一,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恢复原状旨在使已经履行的给付发生清算了结关系,在性质上属于具有债权效力的请求权。(解除权只是变更了合同的债之内容,其债之关系仍然存在,因解除而在内容上变更为“清算关系”。此说现在是德国通说)
至于赔偿损失的性质,由于合同之债仍然存在,所以性质上依然是违约损害赔偿,以履行利益为主。
笔者之前倾向于折中说的观点,认为此种观点有利于解释我国《合同法》之97条,即合同解除和违约责任之间可以并存(详细观点可参见陆青:《合同解除效果与违约责任--以请求权基础为视角之检讨》,载《北方法学》2012年第6期)。
但这种观点,总令笔者仍有疑惑,后思之,还是不赞同这种学说的观点。这种学说下,合同解除后,解除前的合同关系转换为了一种清算关系,但合同的同一性仍然没有变化,就样就容易解释为什么合同解除后还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是,这种合同解除后,合同形态转换的说法,纯粹是一种理论上的拟制,从表面上看,似乎能完美解释法律条款,但是这其实违背了法律体系内在的逻辑性。
笔者目前倾向于直接效果说的观点,合同解除后,合同溯及的消灭,未履行的部分自然免除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予以恢复,难点是恢复原状的性质。如采物权行为有因性的观点,恢复原状应理解为返还原物请求权。又因为合同解除后,已经无法律上的原因,故也可以认为是不当得利返还(给付型不当得利),从而发生返还原物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竞合。
接下来的一个难点是合同既已经溯及的消灭,为何还有赔偿损失的存在?如果存在赔偿损失,其性质是什么?对此,郑玉波教授尝言:“依纯理论言之,原有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过为原债权之变形或扩张,原债权既因契约解除而溯及的消灭,则其损害赔偿请求权,自亦应当归于消灭,德民之所以规定债权人须就解除契约或赔偿请求择一行使者,即贯彻此理论之故;然而因债务不履行所生之损害,究属一种事实,解除权之行使,仅能消灭契约之效力,不能并此事实亦消灭之”(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修订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郑玉波教授的观点,笔者也曾思考到,但笔者当时仍未想明白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之后想到一个勉强的解释方法,即理论上先有损害赔偿(违约责任)的请求,后有解除合同的发生,以此来处理合同解除和损害赔偿的关系。但在当事人先行使解除权,后主张损害赔偿的情形,并不适用。从理论逻辑上来讲,既然合同已经溯及的消灭,此时发生的损害赔偿,应认为其请求权基础是缔约过失责任。
六、附论:解除与风险负担制度的关系问题
在我国合同法上,《合同法》第94条第1项明确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双方都可以解除合同。风险负担规则适用的前提也是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这样,两者就必然存在竞合关系,在发生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履行不能时,既可以适用合同解除制度,也可以适用风险负担规则。
对于学理上一直处于争议状态的两者竞合关系问题,笔者打算找出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谈及风险负担,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何谓风险?从汉语解释上看,风险意味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发生的收益或损失,而立法上仅指损失。既然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与不可抗力便存在有交叉的地方。这也是学理上认为不可抗力和风险负担存在竞合的原因。从合同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合同法》分则设立了相对完整的风险负担规则体系,它针对买卖、租赁、运输、技术开发合同等有名合同,设置了诸多风险负担规则。如我国《合同法》第142条有关买卖合同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承担,第231条租赁合同有关租赁物灭失的风险承担,第314条有关货运合同中货物灭失和运费的风险承担,第338条有关技术开发合同中开发失败的风险承担等。
对于风险负担和不可抗力解除合同的关系,笔者认为,从法律上来看,二者的作用领域不同,风险负担仅仅解决的是风险发生时,该项风险由谁承受,至于风险发生后,合同履行及责任承担等问题,非属风险负担规则管辖。适用风险负担规则后,如履行仍为可能,则继续履行即可,和合同解除规则尚无牵连。只有风险发生后导致履行不能(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才会适用不可抗力解除合同,这是解除合同和风险负担规则竞合之处(于韫珩:《论合同法风险分配制度的体系建构--以风险负担规则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4期,第81页)。
编排/李凌飞
责编/孙亚超 微信号:elesun724